讲座与演出回顾|无需翻译的文化对谈
5月19日,首次来到中国的北爱尔兰暴雨合奏团在北京现代音乐节登台,以一场讲座和一场音乐会带来知识的盛宴。
上午10时,作为合奏团的创团艺术总监,爱尔兰作曲家格里格·卡弗里(Greg Caffrey)携合奏团于中央音乐学院琴房楼演奏厅联袂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这场以《在正统与创新之间:作曲家的创作视角探寻》为主题的作曲讲座将现场演奏与作品实例精妙交织,生动展现了卡弗里对作曲家创作意图的深刻解读,剖析了作曲家视角独特性背后所蕴含的个人经历与背景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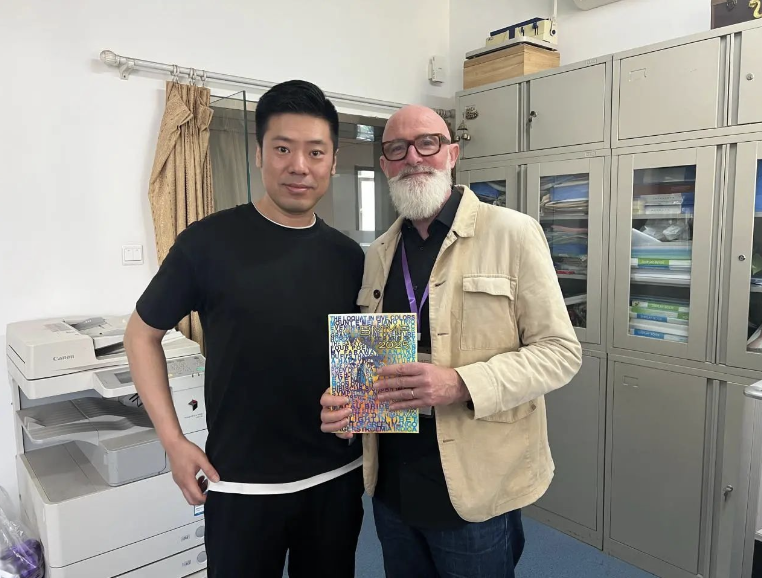
讲座伊始,卡弗里首先介绍了作曲家史蒂夫·莱克(Steve Reich),在聆听莱克作品的过程中,卡弗里巧妙引出一个深刻观点: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并非总是显而易见地跃然于乐谱之上,其往往隐匿于作曲家的个人经历与背景之中。
紧接其后,卡弗里引出他的代表作《落日云蔼》,着重介绍作品的谱面信息与创作意图两者间的关系。在正式展开乐谱谱面分析前,他别出心裁地邀请暴雨合奏团现场演绎该作品的开篇段落。瞬间,灵动的钢琴音符跳跃而出,与弦乐和木管的音色交相辉映,营造出空灵唯美的音响效果。其中,弦乐泛音的精妙运用更为听众勾勒出一幅云雾缭绕、如诗如画的朦胧景致。
在乐谱的谱面分析过程中,卡弗里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作品片段中,有关创作技法层面的两大特色元素。其一是“八音音阶”的巧妙运用,他借此营造出一种如梦似幻、虚实相生的“飘浮”感。其二是弦乐声部的渐强处理,他表示这是为作品注入蓬勃张力的关键所在,使整体音乐在渐强中释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作曲家的创作意图也往往体现在作品的巧思之中。通过卡弗里的介绍得知,如前所述的两大特色元素,不仅是在作品的开篇段落有所体现,更是他贯穿全曲、彰显个性的核心元素。在他看来,创作的技术层面常会受到人文背景的影响,而作曲家选择特定创作技法的个中缘由,往往是整个创作过程中最有趣的部分。这些独特的创作视角实则是作曲家人生经历的鲜活映射,细腻且深刻地体现出他们对生活的独特感悟。

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都会用其独特的视角来诠释作品。卡弗里巧妙地列举了巴赫、梅西安、马勒等音乐巨匠,他们在各自的杰作中倾注心魂,将自身的艺术世界融入到创作之中,使作品成为自我表达与精神探索的载体。卡弗里借此引出他在音乐道路上的正统与非正统的经历,深刻总结出:以乐谱呈现音乐是作曲的技术基础;他学习爵士乐的经历给予他拓宽和声使用的可能;非正统的学习经历则给予在创作过程中无尽的思考空间与灵感源泉。
故从文化层面剖析,《落日云蔼》灵感来源于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歌。作为一首融合叶芝诗歌意境的挽歌式作品,音乐中表达了更为纯粹的失落情感,展现了卡弗里对诗作的个性化诠释和情感投射。作品创作于2013年,是为北爱尔兰暴雨合奏团首场演出而作,因同年一月作曲家的兄长不幸逝世,故此曲中所表达的某种失落亦成为了卡弗里对兄长的深切怀念与真挚献礼。
在讲座尾声,卡弗里凭借其作品《Aingeal》(爱尔兰语,意为“天使”),精彩呈现了他于打击乐与弦乐团运用上的非凡匠心。在随后的提问环节,现场观众热情高涨,围绕作曲家创作意图、作曲创作与观众理解等话题踊跃提问。现场气氛热烈而友好,充分彰显出讲座呈现出的良性互动状态。
本次讲座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技术理性与艺术灵魂碰撞出的探索之旅。格里格・卡弗里以其独特的创作视角,为听众们带来了一场音乐与思想的盛宴,展现了作曲家如何在正统与创新之间探索,如何将个人经历与情感融入音乐创作之中。这场讲座不仅让听众们领略到了音乐的丰富内涵与无限魅力,更激发了大家对音乐创作背后作曲家意图的思考,提供了宝贵的学习与交流机会。
•
讲座结束后,迎来了合奏团的现身说法。当天15:00,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中,北爱尔兰的暴雨合奏团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奏响中国与爱尔兰的八位作曲家的八部现代作品。

从西方乐器对中国音乐气韵的解构与重构,到叶芝诗歌中爱尔兰的神秘浪漫在音符间流淌;从以音乐笔触勾勒霍去病少年英气的东方传奇,到北欧神话的史诗气质在旋律中激荡回响;从对生命本真状态“基调零”的哲学凝视,到音乐与空间场域产生的共振美学……本场音乐会打破地理与文化的边界,不仅是中国与爱尔兰在现代音乐中的深度对话,更是东西方文化体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在音符的交织碰撞中,勾勒出人类共通的情感图谱与审美追求。

音乐会以卡弗雷的《落日云霭》开场,《落日云霭》诞生于卡弗雷对叶芝诗歌《可怖之美诞生了》的深度回应,学界常将叶芝原诗解读为对爱尔兰革命中传统精神在现代性冲击下衰微的安魂曲,但卡弗雷选择剥离历史隐喻,以纯粹的音乐语言聚焦“失落”这一普世情感。
弦乐与木管的交织宛如暮色中的光雾氤氲,作曲家彼时对"空灵美学"的探索在此尽数显现:泛音列的精妙排布模拟诗中"心只求一物,在生命与劳作中变石"的意象,使音响成为悬浮于时间之外的情感容器,引领听众坠入跨越地域的哀婉之境。
值得一提的是,本曲的作曲家也是暴雨合奏团的创始人卡弗雷亲临现场,揭开这部“声音诗篇”的层层面纱,为整场音乐会奠定了一个纯粹与感性的基调。

张书皓的《三匿象》以花的生命韵律为时间轴线,通过三个相互渗透的乐章建构起“含苞”“幽绽”“瞬逝”的声态空间。演奏中频繁出现的长笛的气声技法更加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层次与听觉效果,在原有就活泼跳跃的节奏上更增添了音乐的推动性,如同花茎中暗涌的汁液,终于推动者鲜花绽放。
第二部分中,长笛声部通过循环呼吸构建出花瓣次第舒展的立体声场,钢琴的错位重音如露珠坠落般击碎时间的线性叙事。最终,曲目转为十二音序列的和声基底,长笛的断续音型与钢琴踏板延音交织出“绽放即凋零”的消逝轨迹——声音在持续坍缩中完成对生命本质的哲学追问。作品以微观视角重构植物生长的声态空间,将微分音程、气声奏法、频谱控制的技术实验与诗性隐喻熔铸为一场关于存在与湮灭的听觉仪式。

第三首作品是倪辰康的《炮龙舞》,炮龙节是宾阳县一带汉族、壮族文化融合共生的综合性民族民间节庆。“舞炮龙”即以燃放“鞭炮”弹烧狂舞之龙。民间认为炮烧得越多,龙在自家门前停得越久越吉祥,并认为炮龙节蕴含着祈求风调雨顺、万事如意的寓意。演奏中最出彩的便是对于鼎沸喧嚣的集会场景的描绘,作曲家以音乐的方式渲染出炮声震天,群龙在青烟中翻腾欢舞的景象。

音乐会后的采访中,大提琴演奏家大卫说到,这是整场音乐会中他最感兴趣的作品之一,他震撼于中国龙文化能够以如此惊艳的形式亮相现代音乐作品,同时感叹于作曲家将复杂的大提琴压擦噪音、激烈的拨弦等演奏技法运用与组合,使大提琴的音色开发到了极致,这是作曲家与演奏家不约而同的灵魂碰撞,希望能够在展示中国龙文化的野性与张力,在声学爆破中完成非遗从民俗仪式到当代艺术的跃迁。

音乐会上半场结束自迷雾一般的北爱尔兰神话——安妮塔·莫维尼《玛查的回响》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凯尔特神话中阿尔斯特战争女神玛查的传说。作品的核心织体聚焦于一首脱于原始合唱片段的众赞歌,当混声织体以赋格形式展开,玛查对丈夫克鲁尼乌克的隐秘誓约在复调结构中层层叠现:“勿向世人提及我,因无人知晓玛查能御风而行”。这段源自神话文本的低语,通过弦乐微分音程的特殊处理与高低声部在声场空间中的深度调制,化作穿梭于乐器间的声音幽灵,既暗合女神“不可名状”的神性特质,亦以音乐的复现逻辑隐喻着传说在集体记忆中的永恒回响。

下半场由瑞安·莫洛伊的《戈特纳根二号》开始,该曲是对人与地域、景观之间关联的个性化沉思,深刻探索了归属于某片特定土地的独特体验。乐曲以极具侵略性的长音织体切入,持续的长笛音色被反复徘徊至与人类听觉舒适域共振的频率区间。这种恒定的音高与音色形态,不仅是物理层面的音响存在,更构成了一种听觉意义上的“地域坐标”——当管乐的泛音列与听众脑电波产生同频震荡时,“人与土地联结”这一作品的核心意象已深深地植入观众潜意识。中段,长笛声部慢慢脱离这种音响转而以连续的上行开始演绎更加高亢的旋律,低音单簧管承接中音长笛的频率基干,在低频音域持续深化声音的根基,而长笛所在的高频区旋律的不断升腾又在另一个层面建筑了听觉意义上的精神海拔,这不仅是一个与观众深度链接的声学实验,更是一场关于存在与空间的听觉哲学仪式。

王阿毛的《弄竹弹丝》作为下半场第二首乐曲出现,这部作品原是受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2018年聚焦音乐节委约,为一支西方木管乐器和钢琴而创作的,作品将中国笛箫特有的气震音、颤音、弹舌音等带腔性技法,巧妙链接到西方乐器之上,在键盘的黑白键与木管的音孔间,将中国琴箫艺术的神韵与文人风骨熔铸于西洋乐器的声响体系,其西方音乐中展现的东方气韵随即成为本场音乐会跨越文化边界创作的典范。

琴之古朴、箫之悠远,早已成为东方音乐精神的具象化表达。然而,融合西洋乐器之后的创新尝试亦折射出中西乐器的本质差异。演奏中,演奏者将中国笛箫当中气震音、颤音、弹舌音等中国音乐的独特技法展示的的淋漓尽致,但从乐器的发声材料原理来看,长笛的管壁与笛箫竹质腔体在共鸣结构上存在天然差异,使得高音区的音色表现始终难以企及东方乐器的温润醇厚。恰似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中既有创新突破的惊艳,亦存水土不服的遗憾。这种矛盾与张力,反而让作品成为观察跨文化音乐创作的独特样本,是现代音乐在差异中探寻共鸣的难得尝试。

宋玥的《铁马》是音乐会下半场中的高潮。本曲演绎西汉名将霍去病的传奇事迹。这位汉武帝时期的军事天才18岁即重创匈奴联盟,公元前121年,他两度挥师河西走廊,大破休屠、浑邪二王,为汉王朝掌控战略要地,更开辟丝绸之路北道。班固在《汉书》中记载:“骠骑冠军,飚勇纷纭。长驱六举,电击雷震。饮马翰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祁连。”
本曲叹将军雄姿英发,感名将英年早逝,以精妙的音乐语言勾勒历史画卷。乐曲扑面而来的是融入游牧民族长调民歌元素,草原的苍茫辽阔尽在耳边。小提琴持续的颤弓似河西走廊呼啸的风沙扑面而来,频繁的高音滑音既是战马的嘶鸣,也是刀枪剑戟的碰撞间的金属回响;大提琴坚定的跳弓,仿若霍去病勇往直前的马蹄声,沉稳有力。
瞬间,长笛骤然转为尖锐的短笛,急促的音色如纷飞的战报,千钧一发之际,大提琴却愈发稳健,恰似霍去病临危不惧、坚如磐石的决心。曲终,似应古语所讲“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霍去病23岁英年早逝,在小提琴的蜂鸣中,风沙渐息,沙场重归寂寥,那位少年将军虽已远去,但辽阔草原上,依然回荡着他气吞山河的传奇。

最后,音乐会以一曲杰夫·汉南《突发新闻》作结,以戏谑而尖锐的音乐语言,构建起对电视新闻循环报道机制的深刻批判。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犀利指出,电视媒介的本质决定其难以承载严肃议题,就像烟雾信号无法传递哲学思辨,当电视强行表现严肃时,反而暴露出更深层的荒诞。
这是作曲家对当代媒介生态的音乐性反思。那些破碎且不成乐句的音乐片段,时而以滑稽的分解和声制造荒诞感,时而用故作庄重的柱式和声模拟新闻播报的严肃姿态,正如我们生活中“突发新闻”自四面八方而来的闯入感。随着乐曲推进,各声部愈发密集的交织,宛如信息化浪潮下新闻碎片的增殖,音乐中各种插入段落纷至沓来——在快节奏的信息轰炸中,真实与虚假、重要与琐碎的边界被彻底模糊,最终沦为一场永不停歇的听觉狂欢。《突发新闻》用音乐的棱镜,折射出当代媒介生态的光怪陆离,完成对波兹曼批判理论的音乐诠释。

当最后一个音符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的空间中渐次消隐,掌声如潮,这不仅是对音乐家技艺的致敬,更是对两国现代音乐交流的赞叹。音乐会后的采访中,长笛演奏家与大提琴演奏家纷纷提到了“期待”二字,这种期待早在拿到乐谱的一刻便生发出来,尽管排练时间相当紧迫,暴雨合奏团的各位演奏家仍完美地将所有作品呈现出来。
当不同文明愿意以倾听之姿靠近彼此时,即便乐器不同、文化相异,那些关于纯粹的唯美与热爱,终将在声波的涟漪中,织就一张照亮全球的精神频谱。这或许就是现代音乐的真正意义,八部作品如八面棱镜,在现代音乐与中英文化的交叠中,折射出两个国度的音乐家们对存在、时间、空间的永恒叩问,将这场跨越东西方文明的现代音乐对话凝结为音乐文化的琥珀。

•


项目统筹|郭海鸥
执行助理|张书皓、尹楠
文稿撰写|王一聪、李佳炫
照片摄影|张雅轩、张艺缤
